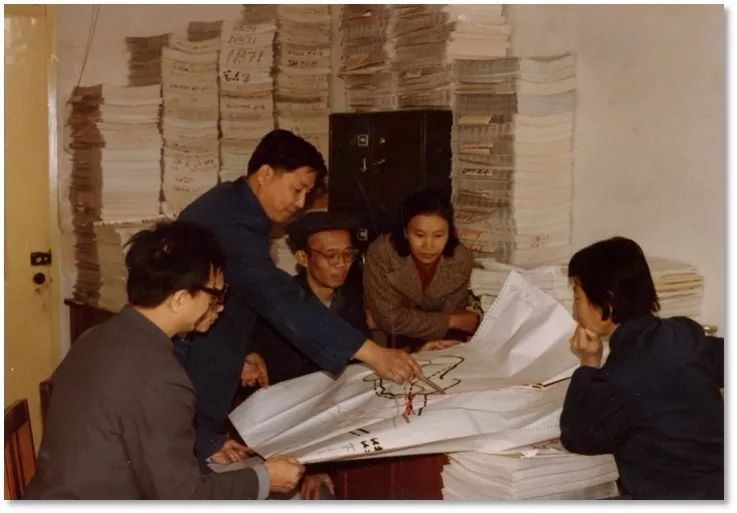60年前,一群热血忠勇之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九所(中物院前身)。几代人历经沧桑,核武器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荒到成绩斐然,其中的艰辛与磨难,世人皆叹。
在这片前辈们取得伟大成就、凝聚产生“两弹”精神的土壤里,究竟有没有一种独特的因素,深藏其中?
要有,那就是中物院人的风骨。
这风骨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无数个怀着科学救国理想、扬名海外却毅然回归的前辈们树立起来的,是从“中国人不必弱于外国人”、白手起家的信念中生发出来的,是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拼搏人生中精炼出来的。
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在60年的时光隧道中,小心呵护和培育着前辈的五样遗存。
一是爱国。爱祖国,就有理想,牺牲名利默默奉献。
二是信心。有信心,就有勇气,艰苦奋斗开创事业。
三是信念。有信念,就有方向,面对目标勇往直前。
四是信任。有信任,就有协作,大力协同披荆斩棘。
五是尊重。有尊重,就有民主,启迪创新成就未来。
因为有这独特的风骨,我们才得以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一代中物院人志存高远,视野更加开阔。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物院的事业继往开来,前景更加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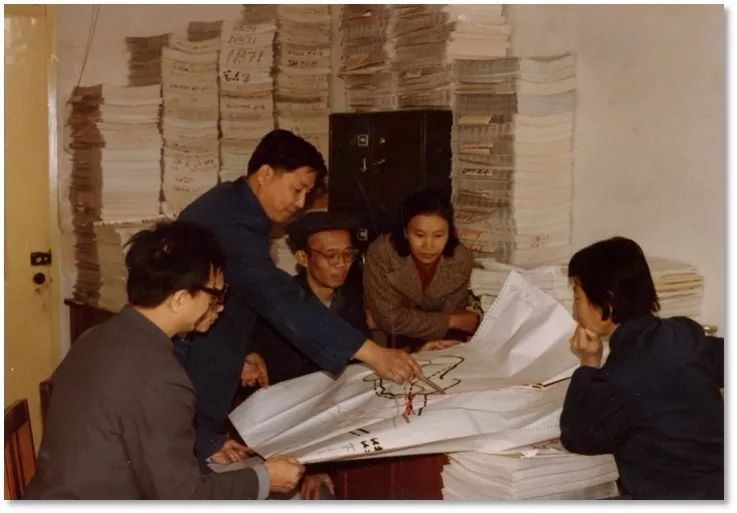
彭桓武先生待人真诚平等,对年轻人既严格又热情,言传身教,发扬学术发主,谁说得对就听谁的。他多次对其他人说:“自己做不了多少,不要妨碍别人。“
1995年10月,彭桓武先生获得100万港币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位在研制核潜艇动力反应堆元件大协作时因吸入放射性粉末得病的同志,给他寄了些钱。后来因医疗改革报销有困难,又一次带钱给他。
1961年7月的一天,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来到朱光亚的办公室,朱光亚以为张副总参谋长专程来检查,张爱萍却朗声笑道:“我不是来听汇报的,而是拜师来了。”朱米亚则连称不敢当。张爱萍说:“是专门来向你请教什么是原子弹的。”朱光亚深为感动,他通俗、详尽地介绍了原子弹方面的科普知识。后来,张爱萍对人们说:“朱副所长的讲课,让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原子弹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朱光亚是我在核工业战线的第一任老师!”
核试验前夕,指挥者和负责人总是高度紧张,有如临深渊之感。在试验现场的一次讨论会上,陈能宽有所触动,忽然脱口背起了《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于敏亦感慨万千,接口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住下背诵,在座者无不肃然恭听,感情起伏波荡。 于敏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传之以心,授之以意,诲人不倦。在理论部,人们总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向于敏请教一个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他不但耐心解答,回到家中还仔细推导,第二天交给年轻人几大页纸,清楚誊写出详尽的推导过程。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彭桓武发现周毓麟在读拓扑学的书,不禁一喜:“我跟你学,咱们一起念吧。”身为“小字辈”周毓麟以为自己听错了。彭桓武说到做到,果然自己先学一遍,然后向周毓麟请教,还将计算题拿给周毓麟批改。 贺贤土回忆:氢弹突破时期,学术民主气氛深厚,人与人之间融洽和谐,没有年龄和资历的差别,只有对科学真理的平等探讨。一次,年轻人沈天海做报告,彭桓武先生也在下面听,中途谈了自己的看法。沈天海赶紧说:“彭公啊,您的思想已经包含在我的思想中了!”下面的听众哈哈大笑,彭公亦莞尔。